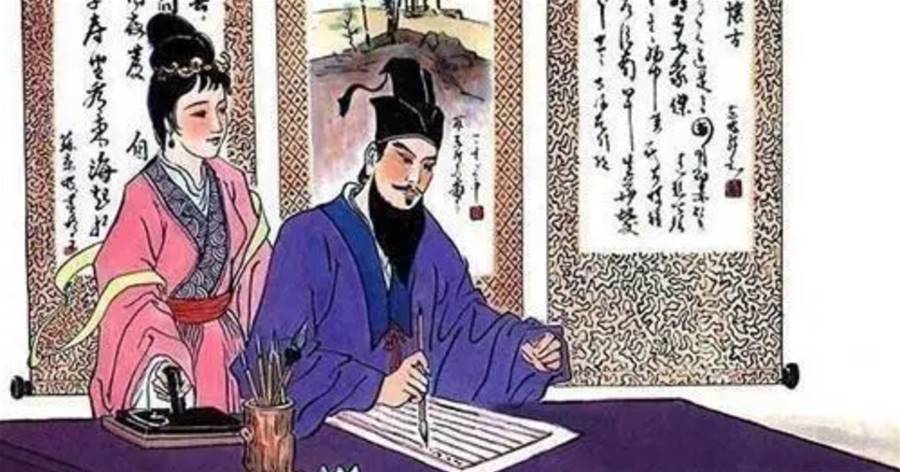
林語堂先生在評價蘇軾時,稱他「這樣的人物,是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」。此言非虛,蘇軾有著令人望塵莫及的才華,善詞、畫、書法,這些他皆是宋一朝的個中翹楚;而與才華相比更令人羨慕的則是他守正不阿、放任不羈的樂天派性格,是他在懷才不遇屢遭貶謫后的不忮不求、順乎自然。
坦白講在歷史長河中,一個人有大才便足以惹人喜愛了;更遑論他還豁達、率真,還「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兒」。而這種性格特點,在宋英宗熙寧六年(1073年)他在杭州通守任上時所作的一首詞中,便體現得淋漓盡致。

杭州,在蘇軾冗長的被貶史中也不過只是一個起點罷了。嘉佑元年(1056年),蘇家父子三人出川赴京,參加科舉考試。
就這樣,在嘉佑二年那場被冠以「千年第一榜」的科舉考試中,蘇軾名震京師。適時,歐陽修權知貢舉,而在看到蘇軾的策論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時他大加贊賞,卻誤以為是弟子曾鞏所書,遂判第二。可在事后方知乃是蘇軾所寫,而在一番攀談后歐陽修對豁達、豪邁的蘇軾有了「文章必獨步天下」的斷言。
可就在蘇軾名動京師之際,母親病故的噩耗傳來。
蘇軾兄弟只得回家奔喪守孝,而在守孝期滿后,蘇軾被授大理寺評事,鳳翔府判官。四年后,他以優異的政績回朝,可父親蘇洵的病逝又讓蘇軾兄弟只得回鄉守孝三年。

而就在三年還朝之后,王安石變法卻已經拉開了帷幕。變法自然就會有「廢立」,有「異同」,此時的朝堂之上歐陽修等人也都被迫外放,但盡管沒有了這些依仗蘇軾卻還是盡顯他的率真性格。
熙寧四年,蘇軾上書直陳變法之弊。而王安石自然不會允許 ,好在他們有的也只是政見上的不同,面對王安石的打壓,蘇軾只得自請出京。
就這樣,蘇軾開始了仕途漂泊之旅。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黃州 、儋州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跡。而杭州就是他的第一站。
按說被外放出京,雖然杭州彼時也是富庶之城,可難免仍有失落才對。可蘇軾卻別是一番模樣。在杭州,署理一應政務之外,他游西湖,觀歌伎,偏偏是樂得快活。初見12歲的王朝云,他便寫下「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妝濃抹總相宜」這等千古名句。
他有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治國抱負,卻又少了他們在那份求而不得后的落拓不安;他有的是亦莊亦諧,是淳樸。于是,你才看見他每到一地在極盡幸事之外總能盡心竭力為地方謀利,修蘇堤、修超然台……。
熙寧六年,在觀瞻了歌伎的舞姿后,蘇軾瞥見了她們的玉足,于是 寫下了一首描寫她們身體部分玉足的詞——《菩薩蠻·詠足》。

菩薩蠻·詠足
涂香莫惜蓮承步。長愁羅襪凌波去。只見舞回風,都無行處蹤。
偷穿宮樣穩,并立雙趺困。纖妙說應難,須從掌上看。
坦白講,這首詞即便是在今天看來用詞上也有一些庸俗,更會令很多女性直叱「惡趣」惱火。可就蘇軾所處的時代以及所表達出的立場而言,我們卻也更要佩服蘇軾的勇氣。
在詞的上片中,開篇兩句便引經據典。以《南史·齊紀下·廢帝東昏侯》中所記載的「蓮承步(即三寸金蓮由來)」來描繪歌伎輕盈的小腳步態。
輕盈的舞步如同旋風一般,都留不下一絲一縷的步履蹤跡。這在中國古代傳統 審美中,并無異議,可這樣的優美背后又是什麼呢?是歌伎們為了滿足這等優美,所被迫進行纏足所帶來的無盡痛苦,是連走路都難以穩健。
關于纏足的起源,眾說紛紜,有隋代說,有五代說、北宋說。《宋史·五行志》中便有記載:「理宗朝,宮人束腳纖直」。

雖然難以求證溯源,但有一點卻是確定的,那就是在宋朝纏足這一對女子身體摧殘的惡習,是盛行起來的。
至于原因,這既有男性的主導地位,理學的興起,亦有文人士大夫的推崇等多種因素導致。
而對于蘇軾而言,他也不免受到影響。否則他也不會在上片中贊美歌伎物資的輕盈;但難能可貴的是這一在當時女子提及都會臉紅的敏感話題,蘇軾卻直接了得指出。
下片中蘇軾便陡然一轉,描寫了歌伎等女子在這份美的背后,確實連雙腳并立而走都困難的現實。單是一句「須從掌上看」蘇軾便帶有著明顯的批判立場的。

人是很難逾越時代鴻溝的。但舉凡大才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,卻總有不凡之處。一如蘇軾,一如這首略顯庸俗的詞。
至于我們后人要做的,也大抵是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」吧。



















